在抗战烽火中的田汉
抗战中,田汉投入左翼文艺运动,并入了党。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呼声日益高涨;同时,国内阶级矛盾也日趋紧张。田汉以其火热的爱国激情,充沛的革命热忱,可谓三日一曲,五日一剧,纵情而来,信笔成篇。从“诗意而浪漫的吟唱”转入“粗野而壮烈的啼声”,其戏剧创作速度之快、数量之高,是相当惊人的。这时期,他写了三个改编剧、十个电影剧本、三部半京剧、两部歌剧、二十七部话剧。其中一些高扬着爱国救亡的主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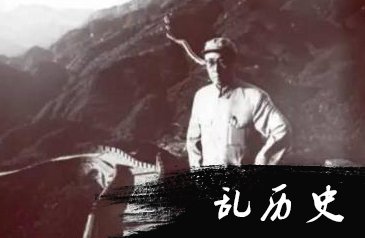
抗战中的田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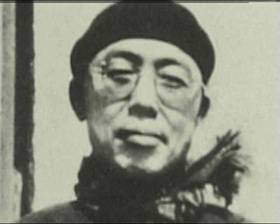
田汉
此时,田汉尝试用戏曲鼓舞民族斗志,用戏曲写历史兴亡之事,以暗合现实动乱之秋。如《明末遗恨》(上)(1937)与《杀宫》(1937),用意在于“亡国”的“教训”,以警醒国人。《土桥之战》与《新雁门关》的题旨,均系“大敌当前,团结为重,谨防汉奸生事”,起来“共救危亡”。
影响更大的,是田汉这一时期的电影剧作。《民族生存》(1933)写一群逃难避灾者无处逃遁,在“一·二八”炮火粉碎了他们的苟安希望之后,发出了愤怒的吼声,延续的是《母性之光》中的意义──个人安危与民族存亡紧紧相联,也是《明末遗恨》所表述的“覆巢之下无完卵”意蕴的复现。
从话剧《火之跳舞》改编过来的《烈焰》(1933)将火灾的社会意义进一步社会化、象征化。“一·二八”之夜炮火引起的熊熊烈火给有闲阶级提供了隔岸观火的“美景”,而民众积极行动起来投身火海“自救”。用两次火灾“烧”出了两个阶级的品质高下,透出了民族斗争、阶级斗争中丢掉幻想、自救自立的积极思想。《青年进行曲》写的是国难、爱情、家丑事件交织在一起时一个叫王伯麟的青年的觉醒与成长的故事。
《风云儿女》(1934)可以说是田汉的杰作。写的是几个从沦陷的东北飘零到上海的东北人,相濡以沫,顽强生存,历经苦难,矢志抗日的故事。塑造出抗日画家梁质夫、诗人辛白华的形象。
在影片中,这首由聂耳谱曲、田汉作词的悲壮的歌,便是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唱出了亿万群众的心声,点燃了中国人民不做奴隶的抗战激情。新中国成立后,田汉回忆说:“《义勇军进行曲》这支歌是作为诗人辛白华《万里长城》长诗的最后一节,紧附在第十五节后面的。但据孙师毅兄说:这支歌不写在故事里面,而是写在另一张包香烟的锡纸的衬纸上的,衬纸被茶叶水濡湿,字迹模糊,他们从衬纸上一字一字地抄下来的。但关于这些,我的记忆跟字迹一样地模糊了。”
这一时期话剧多系社会剧,但是仍然有抗战救亡的剧作。如表现“五·卅惨案”顾正红在率领工人组织与资本家及其走狗斗争中壮烈牺牲场面的《顾正红之死》,显然唤起民众的反帝意识。《水银灯下》(1934)是一出构思巧妙的“戏中戏”。观众在看戏;舞台上又在演“拍电影”的戏。它强调的是抗日民族解放运动的真正舞台在高山密林、丘陵原野,而不在水银灯下、摄影棚内。
歌剧《扬子江暴风雨》(1934)是中国歌剧的奠基之作。它开创了一种新的戏剧样式:幕前朗诵词的背景交代、歌曲与号子的穿插串联、舞蹈表演与剧情推演相结合,丰富多彩又浑然一体,这对中国民族歌剧而言,应该是开创性的。歌剧展示的是上海码头工人作为阶级群体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团结一心、富有组织性与战斗力的形象。歌剧“粗野而壮烈”的音乐旋律,激动人心,演出后唱段不胫而走,唱遍全国。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