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和“一二·一六”:北平学生抗日救亡风云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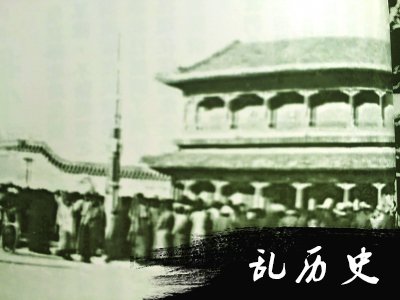
“一二·九”当天,北平爱国学生在新华门前,要求政府出兵抗日。
20多年前,我结识了著名科学家钱伟长和他的妻子孔祥瑛,意外地得知他们相识在一二·九运动清华大学的游行队伍里,一二·九运动是他们的媒人。我把这段历史写进了报告文学《钱伟长》,从1995年元旦开始在《科技日报》连载。当时科技部的部长朱丽兰看到拙作后,每天细心地剪下报纸,攒成厚厚的一沓,亲手送到钱伟长手里。钱伟长向我讲述这段往事时兴奋地像个孩子。从此,一二·九运动这粒种子就深深地埋藏在我的心田。
最近,我系统地采访北平抗战,发现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是北平抗战的一大亮点。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的亲历者、地下党员王若君和知情人刘铁城,走访了运动的亲历者金肇野和吴涛的亲属。中国大学原校友会负责人刘铁城还亲自给我画了北大一二三院在一二·九运动时的方位图。20多年前埋藏在我心灵深处的那粒种子发芽了,波澜壮阔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运动在我的心里长成了一棵参天大树。亲爱的读者,我将用作家的笔如实地告诉您我所知道的故事。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扩大对华北的侵略,策划华北五省(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和二市(北平、天津)脱离祖国独立,华北沦亡迫在眉睫。
北平的青年学生对华北危亡有切身感受,勇敢地冲在第一线。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谷景生、周小舟、彭涛及中共河北省委驻北平特派员李长清等人领导下,在学生中工作的共产党员黄敬、姚依林、郭明秋、宋黎等人积极组织指挥,北平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一二·九和一二·一六抗日救亡运动。
北平地下党催生一二·九运动
北平抗战,一二·九运动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国大学是北平学生抗日运动的基地,1935年11月18日,北平学联在中国大学成立,机关设于北平女一中。此时,北平地下党力量逐渐壮大,积极发动群众,是一二·九运动的催生婆。北平学联在中共地下党的组织下,通过各高校的学生会酝酿更大规模的抗日救国学生运动。
1935年12月8日,一二·九运动的策划会在燕京大学召开,与会者有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东北大学、师范大学、师大女附中、女一中的代表。
1935年12月9日的清晨,北平的街道上寒风刺骨,冷冷清清,行人戴着棉帽,裹着棉袄、棉裤,蹬着棉鞋行色匆匆。北平一片肃杀之气,身穿黑色制服的警察打着哈欠刚刚上岗。突然,从缸瓦市一带的小胡同里冲出了一队打着横幅的学生,这是中国大学学生领袖、共产党员董毓华、白乙化率领的队伍,他们头戴礼帽、围着围脖,身穿长衫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特殊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取消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接着,同学们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同学们手挽手,肩并肩,由北向南行进,董毓华和白乙化走在最前列,董毓华高呼口号,白乙化手举中国大学校旗,雄赳赳气昂昂地前进,100多名学生边走边散发传单。警察前来阻挡,董毓华指着中国大学的校旗说:“我们是中国大学的学生,为了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日本出兵华北,不愿当亡国奴,我们到中南海新华门,向军委北平分会请愿,要求政府抗日。我们这是救亡的正常行为,请放我们过去。”
警察执意不肯,董毓华与地下党交通员联系后发布命令:“目的地是新华门,路遇阻拦可以化整为零,不一定保持队形。”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