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战役再研究:战争前后清廷庙堂都有哪些争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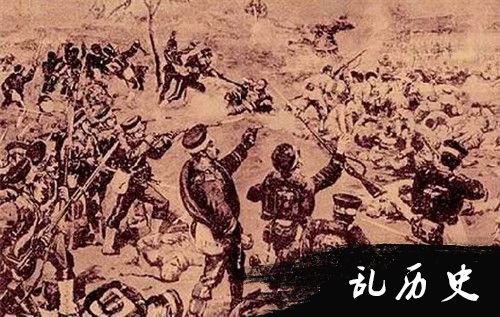
平壤战役 平壤战役是甲午战争陆战中的关键一战,对于战局的影响十分深远。早在开战之前,清廷庙堂之上就存在争议,掌握军权李鸿章主和,因此备受言论的攻击。后来清军进入朝鲜,由于后勤、军纪等众多原因备受困扰,淮军卫汝贵部成为争论的对象,战败之后更成为众矢之的。
关于甲战争前后的政治局势,石泉在其《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一书中剖析颇详,尤其是将视野拓展至甲午战前数十年洋务、清流以及宫廷、朝臣等方方面面,其对开战前夕和战争初期朝中主战、主和舆论以及中枢、北洋等关系把握亦相当到位。至于甲午战争中的平壤战役,除了各种甲午战争史书籍有所涉及外,还有孙克复等人的专篇论文,多以讨论作战为何失败为主旨。本文目的并非检讨甲午平壤之役过程和失败原因,而在于将前敌后勤、作战与后方政局和舆论等因素同时纳入研究视野,并通过对战局和后勤等方面细节的考察,来探究战前用人择将争议、战役过程以及战败后责任追究、战役历史书写的互动情况,从而展现一个更为立体丰富的甲午平壤之役。
一、开战前针对淮军集团的言路攻击
军机大臣翁同龢与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可以说是当时朝廷内外位最高、权最重的汉臣,他们之间的恩怨也为人津津乐道。据说,李鸿章初入曾幕时,以进士妙笔代曾国藩参奏翁同龢之兄翁同书,两人便已结怨。当然,这段双方私人恩怨的故事可靠程度有着不小的争议,但也有人认为此事“自为甲午至戊戌之间一大公案,直关士气与国运之兴衰,非止谈掌故也”。除开这段颇有争议的私人恩怨之外,翁、李分别是当日朝中两大派别的领袖。翁同龢为士林风向,门下有众多名士,如南通状元张謇、两妃之兄志锐以及文廷式等。李鸿章乃洋务主将,不仅主持对外交涉,铁路、电线、矿务、铁甲舰诸端亦多出自李氏之手。抛开守旧趋新之异不论,士林清流和洋务派在言辞上相互攻击,以至于在各种事务上交加肘掣,为晚清政局重要一幕。以李鸿章为首的淮军集团把持北洋军事与洋务事业多年,自然成为士林非议对象,更何况李鸿章的用人原则和淮军集团整体品质偏差也难免成为众矢之的之命运。
至甲午年中日关系紧张,在和、战国策上,李鸿章一意主和,而朝中以翁为首成主战舆论。以青年才俊为主的科道言官和各部小京官纷纷上奏言战,此前力陈停办船械的翁同龢口出“今北洋海陆两军,如火如荼,岂不堪一战耶”之言。翁同龢一意主战的表态,被认为有驱李鸿章入虎口之意,恐怕难逃倾轧误国之责。战前士大夫尤以甲申战事为据,虽承认海军不如人,却颇自负于陆军。如御史庞鸿书于光绪二十年六月十九日( 距丰岛开战仅四日) 上奏以为: “现在与战于朝鲜,正可由陆地进兵,舍我所短,而用我所长。前者越南之役,以法人之桀黠,而镇南关一战,斩首敌酋,军威大振,此前事之可见者也。”
然而,尽管对陆战充满信心,主战派却发现主和持重的李鸿章实为备战之一大障碍。盖因李坐镇北洋二十余年,可以一战的战守常备淮军多在其麾下。掌兵者主和,是主战官员群体必须解决的困境。战端未开时,即有吏科给事中余联沅保举刘铭传、刘锦棠、刘永福、陈湜。除称病在乡的刘铭传外,其他几人均非淮系人马,主战派意在倒淮用湘,利用湘淮矛盾达到抑制李鸿章和积极备战的目的。六月二十日,侍读学士准良称赞宋庆毅军八营“素精训练”,左宝贵“年富力强,不避险阻”,聂桂林“纪律最严,胆气尤壮”。由工部尚书怀塔布代递的郎中端方条陈,明言刘锦棠可用,“殆非刘铭传所可比”。宣战后,又有编修张百熙请刘锦棠以及御史安维峻推荐李秉衡、冯子材、刘铭传、董福祥、刘锦棠等折片。可见,除了甲申抵御法军的刘铭传外,当时北洋陆军主力淮军将领在他们眼中皆不可恃。有的折片还直接参奏淮系人员,比如御史钟德祥六月廿一日有参劾驻日公使汪凤藻的附片。珍妃之兄,与翁氏过从甚密的礼部侍郎志锐,七月初三日有《奏请将丁汝昌等拿交刑部审明正法片》,举荐方伯谦代替丁汝昌统率北洋舰队。若以日后丰岛、大东沟海战中方伯谦临阵脱逃的表现来看,这一主张实属保举非人。刑部侍郎龙湛霖在七月初五日所陈方略四条中之“选将领”一条,言刘锦棠、黄少春、陈湜、魏光焘等湘军将领可用,后又附片参劾刘铭传、丁汝昌。次日,翁同龢的门生、侍读学士文廷式有《奏请将丁汝昌革职拿问治罪片》。七月初九日,御史安维峻在《请饬督臣详查海陆各军目前实情折》中,将丁、刘、叶、卫等前敌后方的陆海淮各军将领议论一过,其奏章遥指的是“督臣”李鸿章。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