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抗战期间王酉亭在重庆的一些往事
如果仅仅说父亲带领“动物西迁”的过程,而不讲他到了重庆后的一些往事,那讲父亲抗战时期在中央大学的经历,似乎是不完整的。
从1938年11月下旬到达重庆算起,抗战胜利后,父亲因在重庆协助处理校产移交及人员物资的安置运送,至到1947年,才最后一批“还乡南京”,共在重庆待了九年的时间;而我的母亲则是在1937年12月5日,带着三个年幼的孩子,跟随中大师生最后一批离开南京到重庆的,她们在1947年和父亲同期回到南京,共在重庆待了十年的时间。

抗战时期在重庆的证件照片
根据父母亲的生前讲述及哥哥姐姐们的回忆,现将父亲在重庆的一些往事记录如下:
我们家在重庆日子里,总体感觉是波澜不惊,异常艰苦。
一是,重庆人满为患。抗战期间,不仅是政府机关和大专院校迁到了重庆,对国民经济有重大影响、对战时军需有保障作用的单位,都迁到了重庆。各地的难民也像潮水般涌入了重庆,加上当地原有的人口,人员是爆炸性地增长。都说当时重庆有几多,即:政府机构多,迁入学校多,兵工厂多,军警多,难民多,到处都可以看到迁入的人员,以及乞讨的流浪者,出了门碰到的大多是外乡人。

抗战期间的重庆人满为患
二是,大轰炸造成了“灭顶”之灾。抗战期间,日军对战时陪都重庆进行长达5年半的数百次轰炸,重庆死于轰炸者万人以上,伤者不计其数,学校与机关被严重破坏,大量民居被毁。每次防空警报一响,大家都争先恐后地往防空洞里跑,场面十分混乱,有的来不及进防空洞的,就近趴在地上听天由命,每次轰炸后都死伤一片,现场哭喊声、呻吟声不断,日军飞机一走,大家都忙着抢救伤者、消防灭火、清理瓦砾、掩埋死者,市民们整天提心吊胆,社会弥漫着恐慌状态,工作与生活秩序极不正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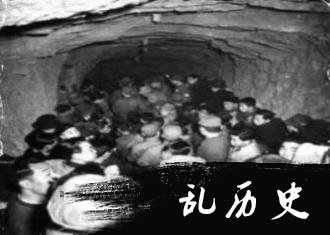
日军对重庆大轰炸,民众躲进防空洞避难,到处火光冲天、死伤不计其数
三是,物资匮乏,生活苦不堪言。战时,生产力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物资本身就严重缺乏,再加上重庆一下涌入那么多的单位和人员,原有的住房和生活必需品远远跟不上需求,造成物价飞涨,连最基本的生活都得不到保障,有些紧缺物资被列为战时管控品。老百姓的日子过的更是艰辛,很多外乡人流离失所,沿街乞讨,屋檐下常栖息着衣不遮体、奄奄一息的难民,能有一个地方住、吃上一口饱饭就是天大的幸事。为了生存,难民们饥肠辘辘四处找活干,可是能被招去用工的寥寥无几,不时有人倒毙街头。家人还经常看到跪在街头挂个牌子卖儿卖女的,有的甚至为了孩子的活命,乞求路人直接将孩子领走,一文钱也不要,嘉陵江上每天都能看到漂浮的死尸,景象惨不忍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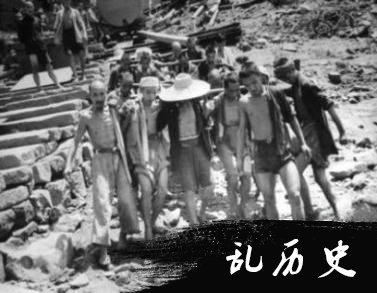
抗战期间重庆的难民时刻在生死线上挣扎
战争在进行,教育在继续,知识在传承,这就是一种民族的希望。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